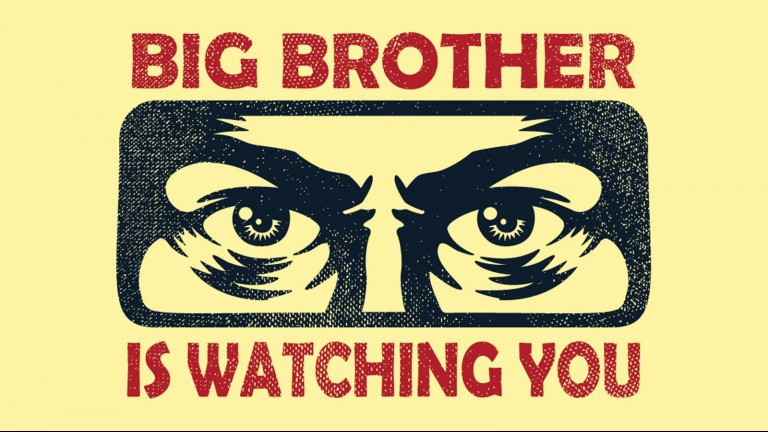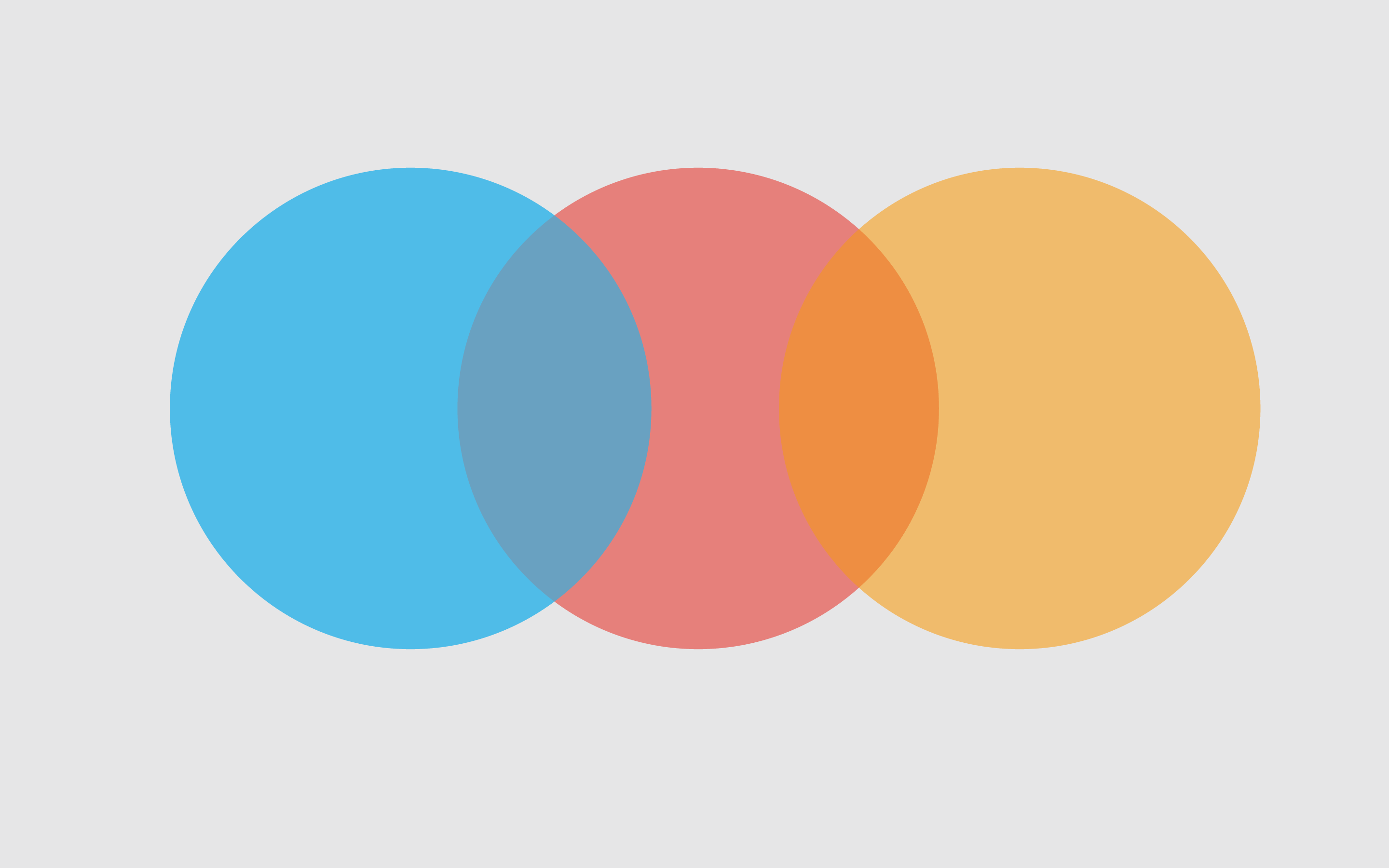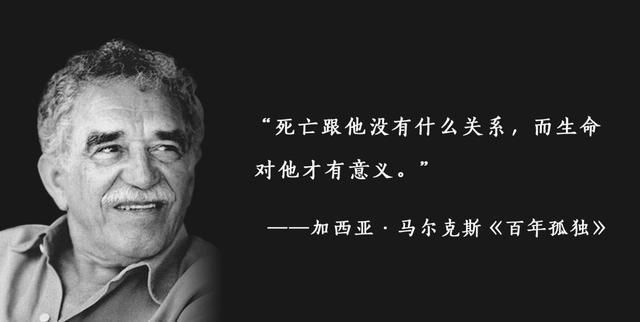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象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,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,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。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,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。
她美丽得恍若梦幻。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。一切如宇宙一般膨胀开来,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。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,同时又全部被削落殆尽。它超越我所知道的所有观念。她和她的耳垂浑融一体,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。
我屏住呼吸,愣愣地看着她。口干得沙沙作响,身体任何部位都出不来声音。白石灰墙壁刹那间仿佛迎面涌来。店内说话声餐具相碰声变成一抹微云样的东西,又重新复原。涛声传来,有一种撩人情思的黄昏韵味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我在几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感受的极小一部分。
看着这电子钟,至少知道世界依然在动。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世界,反正仍持续在动。而只要认识到世界持续在动,我就得以存在。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存在,我也存在。
夜晚暖和得出奇,天空依然阴沉沉的。潮乎乎的南风徐徐吹来。一如往日。海潮味儿同要下雨的味儿混在一起。四周充满令人倦怠的亲切。河道的草丛中虫声四起。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。下的将是看不出下还是不下的牛毛细雨,却会把身体上下淋湿。
在水银灯隐约的白光中可以看见河流。水很浅,刚可没踝,同以往一样清澈。是打山上直接下来的,无从污染。河床里铺满打山上冲下来的石子和沙拉拉的沙砾,处处有阻止流沙的飞瀑。瀑下有深水坑,小鱼在里面游动。
水少时河流整个被沙吸进去,唯有散发着微微潮气的白沙路剩在那里。我曾借散步之便沿这条白沙路溯流而上,寻觅河水被河床吸入的起点。河流的最后一条细涓像忽然发现什么似的止住不动,而下一瞬间即已不见。地底的黑暗它们吞了进去。
当个人认识同进化连续性这两根西欧人文主义支柱失去意义的时候,语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。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,而是作为混沌状态存在。你这一存在就不是独立特立的存在,而不过是混沌罢了。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,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。存在就是交流,交流即是存在。
我用手指悄悄拨开她的秀发,吻在她的耳朵上。世界微微摇颤。小小、小而又小的世界。时间在那里如温和的风一般流逝。
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,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。建筑物看上去俨然如摄影棚里的布景,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。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,如炮弹一般在天空中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。
所以我一直以为人生就是那么一种东西,就是要四处寻找什么,那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但实际目睹曾几百次从照片上看到的这片风景,觉得甚是奇妙。其纵深竟是那样的造作,与其说是赶到了这里,倒不如说是谁按照照片匆忙在这里造出了一片临时风景。
时间在流逝。黒粒子在我的视网膜上描绘出奇异的图形。不出片刻,原来的图形悄悄崩溃,由别的图形取而代之。水银般静止的空间里,唯独黑暗在动。
我止住思考,把自己交给时间的河流。时间不断地冲着我走。新的黑暗描绘新的图形。
涛声传来。冬天滞重的波涛。铅色的大海和女人后颈般莹白的海波。冻僵的海鸥。
“羊”代表着什么?
为什么最后总是不经意出现海波,涛声?
鼠说:“只是她恐怕再也不能再吸引你了,我也觉得不忍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消失了,她身上的什么完全消失了。”
所以那位女孩身上消失的是“耳朵”?